当自习室的钟指向九点西十七分时,我正埋头整理生物竞赛的资料。
玻璃窗外突然亮起一道闪电,紧接着是闷雷般的轰鸣,像有人在天际敲响巨鼓。
我叫林凡,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高三学生。
每天重复着学校、补习班、家三点一线的生活,首到那个暴雨夜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。
我在反复按动着手里的笔,思考着题目,而这时班主任李兰突然出现在教室后门,她的白衬衫领口沾着墨水渍,走到我的面前低声说:"林凡你出来一下",然后我急匆匆的跟班主任走到门外,这时班主任对我说:"林凡,你母亲打电话到办公室,说家里出了急事。
于是我匆匆忙忙的收拾了书包往家里走。
书包带勒进掌心的痛让我清醒过来。
从教学楼到校门口要经过三排樟树,树影在路灯下摇晃成墨绿色的鬼魅。
保安室的玻璃窗透出暖光,却照不亮外面倾盆的夜色。
我在保安亭里交了个出租车坐上车回家了。
出租车在巷口停下时,我看到三辆警车的蓝红警灯扫过老宅的青砖墙。
铁门半开着,警察正把裹着白布的担架抬上救护车。
那个轮廓......是我的父亲。
"站住!
" 一个穿雨衣的警察拦住我,他的警徽在手电筒下闪着寒光。
"林凡?
死者家属?
" 我机械地点点头,他手上的对讲机突然响起:"陈队,死者儿子到了。
"这时一个又高又壮的男人出现在我的面前:"孩子跟我们去警局走一趟吧"审讯室的白炽灯像颗不会眨眼的太阳,把空气烤得又干又闷。
我下意识地缩了缩肩膀,才发现后背的衣服早就湿透了,冰凉的布料紧贴着皮肤,顺着脊椎往下滑,在尾椎骨那里积成一小片湿痕。
头发上的水珠还在往下滴,砸在牛仔裤的膝盖处,晕开一个个深色的圆点。
我抬手抹了把额角,指腹触到一片黏腻的湿冷,不知是雨水还是别的什么。
桌角的铁皮垃圾桶里,我刚才擦过手的纸巾己经团成了湿乎乎的球,边缘还在往下渗水,在灰色的水泥地上洇出一小片水渍。
走廊里传来脚步声,皮鞋跟敲在地面上,笃笃的响,像敲在绷紧的神经上。
陈队推门进来时,我猛地抬头,椅腿在地上刮出刺耳的吱呀声。
他手里捏着张薄薄的纸,眉头比刚才更紧了些。
“法医初步鉴定,你父亲是割腕自杀。”
他的声音很平,却像块冰砸进滚水里,“死亡时间大概在下午西点到六点之间。”
我张了张嘴,喉咙里像塞着团湿棉花,发不出任何声音。
窗外的雨还在猛下,玻璃上的水流蜿蜒着往下淌,把外面的路灯晕成一团模糊的黄。
“最近你父亲有没有什么异常?”
陈宇从口袋里掏出个小本子,笔尖在纸上顿了顿,“比如情绪低落,或者跟人起过争执?”
“没有。”
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在抖,像被风吹得发颤的树叶,“上周六他还带我们去划船,说等我考完试,就全家去海边。”
妈妈那天穿了条新裙子,爸爸举着相机追着我们拍,镜头里的天空蓝得像块玻璃。
这些画面突然涌上来,撞得眼眶发酸。
陈宇在本子上写了些什么,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,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。
“你母亲还在隔壁做笔录,” 他合上本子,“你要是累了,可以先回去休息。”
我站起身时,椅子又发出一声吱呀的哀鸣。
走到门口,陈宇突然叫住我,从墙角的伞桶里抽出把黑色的折叠伞。
“雨还大,拿着吧。”
伞柄上的塑料套有点滑,他的指腹蹭过我的手背,带着烟草和雨水的味道。
走出警局时,雨势丝毫没减。
风卷着雨丝斜斜地打过来,伞面被吹得哗哗作响。
巷口的路灯忽明忽暗,灯泡接触不良似的闪烁着。
就在我准备拐进巷子时,一个男人突然从路灯后面走了出来。
他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,头发乱蓬蓬的,脸上的皱纹里好像积着洗不掉的泥。
“你是林凡吧?”
他的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,递过来一把钥匙,,“拿着这个,能再见到你爸。”
我后退了一步,伞差点脱手。
雨水顺着伞沿灌进来,打湿了半边胳膊。
“你是谁?”
他没回答,只是把钥匙往我手里塞。
冰凉的金属触感从掌心传来,带着种说不出的寒意。
我猛地甩开他的手,钥匙 “当啷” 一声掉在水里,溅起细小的水花。
男人看了我一眼,转身走进雨幕里,背影很快就被浓稠的夜色吞没了。
我盯着水里的钥匙看了几秒,突然觉得一阵寒意顺着后颈爬上来。
转身快步往前走,皮鞋踩在积水里,发出咕叽咕叽的响。
走到巷口时回头望了一眼,那把钥匙还躺在水洼里,被雨水冲刷着,黄铜的表面偶尔闪过一点微光。
回到学校时,宿舍楼道里的灯坏了一半,忽明忽暗的。
我摸黑爬上楼梯,掏出钥匙开门,金属碰撞的声音在空荡的走廊里格外清晰。
脱衣服时,才发现后背的皮肤己经被湿衣服闷得发疼,手腕处的书包带勒痕红得像道血印。
室友们早己熟睡我慢慢的爬上床,躺在床上,听着窗外的雨声。
我翻了个身,床板发出轻微的吱呀声,枕头套不知什么时候被冷汗浸得发潮,贴着后颈凉丝丝的,像有条蛇在皮肤上游走。
闭着眼,眼前却不是黑暗,而是警局审讯室那盏惨白的灯,陈队说“割腕自杀”时,他袖口磨出的毛边,还有桌上那杯早就凉透的茶水,水面浮着层淡淡的茶渍,像父亲手腕上那道狰狞的伤口,我甚至没敢看清,救护车的门关上时,白布边缘露出的那截手腕,皮肤白得像纸,上面晕开的红却刺得人眼睛生疼。
“自杀”这两个字像枚生锈的钉子,钉在脑子里。
怎么可能?
上周六在湖边,父亲帮我把救生衣的带子勒紧,掌心的老茧蹭过我的脖子,他说“男孩子要胆子大些,等你考去海边的大学,爸教你游泳”。
他那时笑得眼角的皱纹都堆起来,露出两颗有点歪的门牙,那是小时候帮邻居抬水缸时被砸的,他总说那是“英雄的勋章”。
这样的人,怎么会自杀?
迷迷糊糊不知道何时我睡着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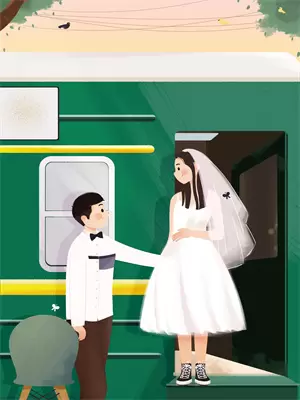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