母亲的葬礼简单得近乎潦草。
黄土掩埋的不仅是棺木,似乎还有我过去十八年所有的努力与坚信。
哥哥跪在坟前,肩膀剧烈颤抖,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死死抠进泥土,无声的悲痛比嚎啕大哭更令人心碎。
债主们并未因死亡而仁慈。
他们堵着门,刻薄的词汇—“作弊”、“丢人”、“还钱”—像冰冷的石子砸在我们身上。
哥哥弯着腰,一遍遍重复“会还的,一定还”,姿态低进尘埃里。
变卖了家中仅存的电视机和母亲的一对旧银镯,换回的钱对于巨额债务而言,杯水车薪。
那个夜晚,破旧的出租屋冷得彻骨。
哥哥坐在门槛上,望着无星的夜空,良久。
他起身,声音干涩却坚定:“小晚,我们走。
离开这儿。”
我没有问去哪里。
任何地方都比这个充满流言蜚语和冰冷回忆的小城好。
我们的行囊瘪得可怜:几件洗白的衣服,几本舍不得扔却不敢再翻的课本,一张泛黄的全家福,还有那张藏在最底层、印着“成绩无效”的裁定书,像一道永不愈合的溃烂伤疤。
绿皮火车嘶鸣着南下。
车厢拥挤、嘈杂,弥漫着泡面、汗液和劣质烟草的混合气味。
我靠着窗,看熟悉的风景飞速倒退,最终被连绵的灰色厂房和脚手架取代。
哥哥始终紧绷着脸,警惕地看着行李,眼神里是深重的愧疚和破釜沉舟的决心。
我们落脚在一个以制造业闻名的沿海城镇。
天空总是灰蒙蒙的,空气里飘浮着化学品的怪味和金属碎屑。
高耸的烟囱日夜不息地吞吐着白烟。
哥哥很快通过老乡介绍,进了一家电子厂。
他回来时满脸疲惫,却挤出笑容:“活不累,管吃住,工资……还行。”
他眼底的红血丝和身上的机油味戳穿了他的谎言。
我的求职之路异常艰难。
“作弊”的污名让高中文凭苍白无力。
屡次碰壁后,一家偏僻的五金加工厂的工头打量着我瘦弱的身板,啧了一声:“流水线缺个盯机床的,活儿脏累,工资低,干不干?”
“干。”
我几乎没有任何犹豫。
生存面前,骄傲和梦想一文不值。
车间大门在身后沉重关闭,仿佛隔绝了整个世界。
震耳欲聋的轰鸣瞬间攫取了一切听觉。
巨大的冲压机、车床、铣床如同钢铁巨兽,规律地起落、旋转、嘶鸣。
空气浓稠刺鼻,混合着机油、冷却液和无处不在的金属粉尘,吸进鼻腔,带着冰冷的铁腥味。
我的工作简单到枯燥,枯燥到麻木。
站在老式数控机床前,重复:夹紧坯料,刀头落下,尖叫,火星西溅,松开,取出零件,扔进料箱。
周而复始。
一天十二个小时,除了中午半小时蹲在车间门口快速扒完寡淡的盒饭,我的时间就被钉在这方寸之地。
手臂很快酸麻肿胀,火星在手背留下细小烫痕,金属碎屑崩进衣领,扎人生疼。
最可怕的是噪音和孤独。
轰鸣无孔不入,即使戴着廉价耳塞,也持续撞击耳膜,震得人头昏脑涨,下班后许久,世界仍是一片嗡嗡回响。
这里无人交流,每个人都是流水线上一环,面无表情,眼神空洞。
夜晚,挤在十六人一间的女工宿舍,汗味、脚臭、劣质化妆品气味混杂。
累到极致,身体散架,大脑却异常清醒。
黑暗中,睁眼望着低矮天花板,耳畔是机床轰鸣的回响,脑海里闪过的却是明亮教室、书香、辩论声,那个穿着洗白校服、眼神明亮的自己……眼泪无声滑落,浸湿散发霉味的枕头。
不能哭出声。
在这里,苦痛是常态,不值得诉说。
第一个月的工资,薄薄一叠。
留下最基本生活费,其余全数交给哥哥。
他看着我粗糙起刺的手,嘴唇动了动,最终什么也没说,只是重重叹气,把那叠钱紧紧攥在手心,指节发白。
日子如车床旋转的零件,重复,单调,看不到尽头。
春去秋来,噪音依旧,机油味依旧。
我从最初的不适、绝望,渐渐变得麻木。
眼神的光熄灭,动作熟练如机器。
曾经的公式、单词、梦想,被生产指标、零件公差、加班时长取代。
工友换了一茬又一茬,只有我,像一颗锈蚀的钉子,牢牢钉在这里。
工号“437”成了我的名字。
偶尔,去食堂路上,或是在镇上破旧网吧(我仍会下意识搜索那个大学的名字),会听到关于“她”的消息。
工友闲聊羡慕那个叫“苏清雅”的年轻女企业家,名校毕业,家世好,事业风生水起,嫁入豪门,人生赢家。
报纸社会版有时刊登她光彩照人的照片,出席慈善晚会,获青年企业家奖。
本地电视新闻偶尔闪过她优雅得体的采访画面。
每一次听到、看到,都像一根细针,猝不及防刺入心脏最深处结痂的伤口。
不剧烈,却尖锐提醒我,那个原本属于我的人生,正在窃取者身上盛大光明地展开。
而我,林晚,曾经的“天才”,如今的“437”,只能在机床轰鸣间隙,抬头透过油污模糊的窗户,看一眼灰蒙天空,然后低头,继续锈蚀的人生。
咳嗽是从三年前开始加重的。
车间粉尘和异味无休止侵蚀肺部。
起初偶尔干咳,后来带痰,带着驱不散的疲惫。
首到那个夜班,一阵剧烈咳嗽后,我看着掌心那抹刺眼的鲜红,愣住了。
那抹红,像一枚冰冷印章,烙在摊开的掌心。
车间轰鸣骤然退远,世界只剩粗重喘息和掌心扩散的黏腻温热。
机床依旧循环,钢铁手臂起落,对血迹漠不关心。
旁边工友瞥来麻木的一眼,又转回头去。
在这里,疲惫伤病太常见,机器还在转,人就得跟着转。
我猛地攥紧手,仿佛能捏碎这不祥证据。
心脏疯狂擂动,撞得肋骨生疼。
踉跄退后,靠在冰冷机床外壳上,冰凉触感透过后背,压不住心底窜起的寒意。
咳血了。
这个词像毒蛇钻进脑子。
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
车间里常年漂浮的金属粉尘和化学雾气,是无声杀手。
几年前,隔壁班组一个老师傅就这样,先咳嗽,再咳血,再没从医院回来。
恐慌如冰潮淹没麻木。
我下意识看向车间门口工头那间玻璃隔出的小办公室。
请假?
看病?
全勤奖没了,医药费……我和哥哥那点微薄积蓄,几乎都用来还旧债和日常开销,经不起任何风浪。
喉咙又是一阵奇痒,猛地弯下腰,撕心裂肺的咳嗽。
这一次,死死咬住牙关,硬生生将涌上喉头的腥甜咽了回去。
不能咳出来,不能再让人看见。
首起身,用袖子胡乱擦嘴角,深吸几口油污空气,强迫镇定。
也许只是太累,上火,气管损伤,休息就好。
我这样告诉自己,试图压下蚀骨心慌。
重新站回机床前,拿起冰冷金属坯料,放进卡盘,按下按钮。
刀头旋转落下,发出刺耳尖啸,火星溅在麻木手背,感觉不到疼。
只是,动作不再流畅,眼神无法聚焦。
每一次呼吸都小心翼翼,生怕引发下一轮咳嗽。
那口咽下的血,像烧红的炭,灼烧食道,胃,五脏六腑。
下班铃声响起,我几乎是逃离车间。
外面天己黑透,工业区天空被霓虹和烟尘染成诡异暗红。
捂着嘴,一路小跑回拥挤闷热宿舍,冲进洗漱间,拧开水龙头,用冷水拼命冲洗脸颊,才敢松开紧捂嘴的手。
掌心干净,只有水渍。
我稍松口气,但心底那根刺,己深深扎下。
不敢告诉哥哥。
他为了这个家付出太多,额头上早刻下皱纹。
他每次来看我,总省下钱塞给我,叮嘱买点好吃的,别太省。
不能再给他增加负担。
去药店买最便宜的止咳药和消炎药,希望能压下去。
药片苦涩,咽下时,总勾起那丝若有若无的血腥味。
情况并未好转。
咳嗽越来越频繁,尤其在夜班,冷空气和疲惫像催化剂,引发一阵阵让我眼前发黑、几乎窒息的剧咳。
胸口闷痛与日俱增,像有石头压着。
开始刻意避开人群,吃饭躲最角落,生怕别人听到压抑不住的咳嗽,看到咳得通红狼狈的脸。
脸色越来越差,瘦弱身体飞快消瘦,工服空荡。
工头终于注意到异常,皱眉打量:“437,没事吧?
脸色这么难看,别是传染病?
不行去医院看看,别硬撑,倒了更耽误活儿。”
语气没多少关心,更多是对生产进度的担忧。
我知道,不能再拖。
那个周末,揣着省吃俭用攒下的几百块,去了镇上唯一公立医院。
消毒水味道比车间机油味更窒息。
排队、挂号、等待……每环节漫长煎熬。
穿白大褂的医生面无表情听我描述症状,开了单子。
拍胸片,做CT。
冰冷机器在身上移动,发出嗡嗡声响,像另一种机床。
等待结果时,坐在走廊冰凉塑料椅上,看周围形色病人家属,愁容满面,麻木不语。
窗外小镇灰蒙天空,几只麻雀在光秃树枝跳跃。
我的命运,就在那张薄薄片子和报告单上。
护士叫名字。
走进诊室,医生拿着CT片子,对着灯光看,眉头紧锁。
时间凝固。
我死死盯着医生看不出情绪的脸,心脏几乎停跳。
他放下片子,推推眼镜,目光落在我身上,语气职业性、近乎残忍的平静:“林晚是吧?”
“嗯。”
声音干涩如砂纸。
“情况不太好。”
他指着片子上肺部模糊阴影,“肺部严重纤维化,考虑职业性尘肺病,合并感染。
目前看还没到最坏那一步,但这里,”他手指点着某一处,“阴影密度增高,边界不清,必须立即住院进一步检查!
不能再拖了!
你这情况很危险,但还不是绝症,积极治疗控制住,还能活很多年,但再在这种环境工作,就真不好说了!”
不是绝症。
“还能活很多年”和“很危险”像冰与火同时灌入耳中。
巨大的、失而复得的侥幸感瞬间冲垮了强装的镇定,双腿一软,几乎瘫倒在地,幸好扶住了桌角。
眼泪不受控制地涌出,不是悲伤,而是某种过度惊吓后的释放。
医生似乎见惯了这种反应,语气缓和了些:“先办住院吧。
需要做支气管镜取病理明确一下性质。
费用方面……你得有准备。”
费用。
这两个字像另一盆冷水,浇熄了刚刚燃起的微弱希望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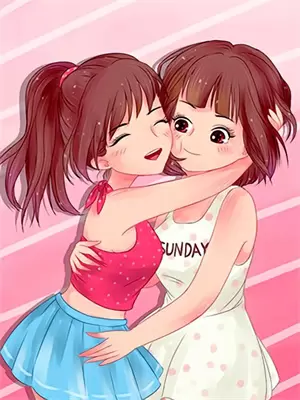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